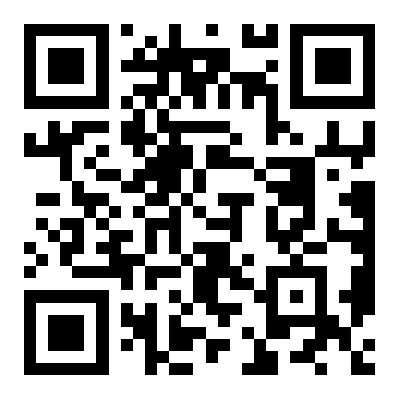辯論,是把對人進行考查后所作的鑒定加以認真分析。彼此用一定的理由來說明自己對事物或問題的見解,揭露對方的矛盾,以便最后得到正確的認識或共同的意見。
辯論技巧的三大要素:
1.辯論中存在著持不同意見的雙方或多方。有不同意見的雙方或多方存在才能實現思想交鋒。一個人不可能自己同自己辯論,一個人頭腦中幾種方案或做法的權衡和比較,那是思考或思辨而不是辯論。
2.辯論必須針對同類事物或同一問題,即存在著同一論題。如果各方談論的論題不同,就不能實現有意義的辯論。例如,一個人說“法律是有階級性的”,一個人說“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由于兩人所認識的對象不同,因此兩個觀點不能構成辯論。只有當一個人說“法律是有階級性的”,另一個人說“法律是沒有階級性的”這樣兩個判斷才構成辯論。因為這兩個判斷所認識的對象相同,又是相互對立的思想,而這兩個判斷至多只能有一個為真,不可能都真。這樣就有了誰是誰非的問題,就必然要引起辯論。
3.辯論的諸方有或多或少的共同認識或共同承認的前提,如思維的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以及正確推理的方法等,以及如社會公理、科學規律等是非真偽標準和價值取向。沒有這些共同承認的東西,辯論只會是一場混戰,不可能得出結論。總之,辯論諸方有共同的話題,而又有不同意見。從哲學觀點看,辯論的諸方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見到如下情況:當消防隊接到求救電話時,常會用慢條斯理的口氣來回答,這種和緩的語氣,是為了穩定說話者的情緒,以便對方能正確地說明情況。又如,兩口子爭吵,一方氣急敗壞,一方不焦不躁,結果后者反而占了上風。再如,政治思想工作者常常采用“冷處理”的方法,緩慢地處理棘手的問題。這些情況都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慢”也是處理問題、解決矛盾的好辦法。論辯也是如此,在某些特定的論辯局勢下,快攻速戰是不利的,緩進慢動反而能制勝。
例如,1940年,丘吉爾在張伯倫內閣中擔任海軍大臣,由于他力主對德國宣戰而受到人們的尊重。當時,輿論歡迎丘吉爾取代張伯倫出任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認為自己是最恰當的人選。但丘吉爾并沒有急于求成而是采取了“以慢制勝”的策略。他多次公開表示在戰爭爆發的非常時期,他將準備在任何人領導下為自己的祖國服務。
當時,張伯倫和保守黨其他領袖決定推舉擁護綏靖政府的哈利法克斯勛爵作為首相候選人。然而主戰的英國民眾公認在政壇上只有丘吉爾才具備領導這場戰爭的才能。在討論首相人選的會議上,張伯倫問:“丘吉爾先生是否同意參加哈利法克斯領導的政府?”能言善辯的丘吉爾卻一言不發,足足沉默了兩分鐘之久。哈利法克斯和其他人明白,沉默意味著反對。一旦丘吉爾拒絕入閣,新政府就會被憤怒的民眾推翻。哈利法克斯只好首先打破沉默,說自己不宜組織政府。丘吉爾的等待終于換來了英國國王授權他組織新政府。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概括出在論辯中要正確使用“以慢制勝”法,至少要注意以下三點:
其一,以慢待機后發制人
俗話說:“欲速則不達。”在時機不成熟時倉促行事,往往達不到目的。論辯也是如此,“慢”在一定條件下也是必須的。“以慢制勝”法實際上是論辯中的緩兵之計,緩兵之計是延緩對方進兵的謀略。當論辯局勢不宜速戰速決,或時機尚不成熟時,應避免針尖對麥芒式的直接交鋒,而應拖延時間等待戰機的到來。一旦時機成熟,就可后發制人,戰勝論敵。如在例子中,丘吉爾在時機不成熟時,不急于成功,以慢待機。在討論首相人選的關鍵時刻,以沉默表示反對,最終贏得了勝利。
其二,以慢施謀以弱克強
“以慢制勝”法適用于以劣勢對優勢、以弱小對強大的論辯局勢。它是弱小的一方為了戰勝貌似強大的一方而采取的一種謀略手段。“慢”中有計謀,緩動要巧妙。這里的“慢”并非反應遲鈍,不擅言辭的同義語,而是大智若愚、大辯若訥的雄辯家定計施謀的法寶之一。如在例子中,丘吉爾面對張伯倫的追問,裝聾作啞,拖延時間,實際上是假癡不癲的緩兵之計。在這一種韌性的相持中,張伯倫一方終于沉不住氣了,丘吉爾以慢施謀終于取得了勝利。
其三,以慢制怒以冷對熱
“慢”在論辯中還是一種很好的“制怒”之術。論辯中唇槍舌劍,自控力較差的人很容易激動。在這種情況下,要說服過分激動的人,宜用慢動作、慢語調來應付。以慢制怒,以冷對熱,才能使其“降溫減壓”。只有對方心平氣和了,你講的道理他才能順利接受。
總之,論辯中的“快”與“慢”也是一種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兵貴神速,“快”當然好。可是,有時“慢”也有“慢”的妙處。“慢”可待機,“慢”可施謀,“慢”可制怒。“慢”是一種韌性的戰術,“慢”是一場持久戰,“慢”是舌戰中的緩兵之計。緩動慢進花的時間雖長,繞的彎子雖大,然而在許多時候,它卻往往是取得勝利的捷徑。
辯論技巧的三大要素:
1.辯論中存在著持不同意見的雙方或多方。有不同意見的雙方或多方存在才能實現思想交鋒。一個人不可能自己同自己辯論,一個人頭腦中幾種方案或做法的權衡和比較,那是思考或思辨而不是辯論。
2.辯論必須針對同類事物或同一問題,即存在著同一論題。如果各方談論的論題不同,就不能實現有意義的辯論。例如,一個人說“法律是有階級性的”,一個人說“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由于兩人所認識的對象不同,因此兩個觀點不能構成辯論。只有當一個人說“法律是有階級性的”,另一個人說“法律是沒有階級性的”這樣兩個判斷才構成辯論。因為這兩個判斷所認識的對象相同,又是相互對立的思想,而這兩個判斷至多只能有一個為真,不可能都真。這樣就有了誰是誰非的問題,就必然要引起辯論。
3.辯論的諸方有或多或少的共同認識或共同承認的前提,如思維的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以及正確推理的方法等,以及如社會公理、科學規律等是非真偽標準和價值取向。沒有這些共同承認的東西,辯論只會是一場混戰,不可能得出結論。總之,辯論諸方有共同的話題,而又有不同意見。從哲學觀點看,辯論的諸方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見到如下情況:當消防隊接到求救電話時,常會用慢條斯理的口氣來回答,這種和緩的語氣,是為了穩定說話者的情緒,以便對方能正確地說明情況。又如,兩口子爭吵,一方氣急敗壞,一方不焦不躁,結果后者反而占了上風。再如,政治思想工作者常常采用“冷處理”的方法,緩慢地處理棘手的問題。這些情況都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慢”也是處理問題、解決矛盾的好辦法。論辯也是如此,在某些特定的論辯局勢下,快攻速戰是不利的,緩進慢動反而能制勝。
例如,1940年,丘吉爾在張伯倫內閣中擔任海軍大臣,由于他力主對德國宣戰而受到人們的尊重。當時,輿論歡迎丘吉爾取代張伯倫出任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認為自己是最恰當的人選。但丘吉爾并沒有急于求成而是采取了“以慢制勝”的策略。他多次公開表示在戰爭爆發的非常時期,他將準備在任何人領導下為自己的祖國服務。
當時,張伯倫和保守黨其他領袖決定推舉擁護綏靖政府的哈利法克斯勛爵作為首相候選人。然而主戰的英國民眾公認在政壇上只有丘吉爾才具備領導這場戰爭的才能。在討論首相人選的會議上,張伯倫問:“丘吉爾先生是否同意參加哈利法克斯領導的政府?”能言善辯的丘吉爾卻一言不發,足足沉默了兩分鐘之久。哈利法克斯和其他人明白,沉默意味著反對。一旦丘吉爾拒絕入閣,新政府就會被憤怒的民眾推翻。哈利法克斯只好首先打破沉默,說自己不宜組織政府。丘吉爾的等待終于換來了英國國王授權他組織新政府。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概括出在論辯中要正確使用“以慢制勝”法,至少要注意以下三點:
其一,以慢待機后發制人
俗話說:“欲速則不達。”在時機不成熟時倉促行事,往往達不到目的。論辯也是如此,“慢”在一定條件下也是必須的。“以慢制勝”法實際上是論辯中的緩兵之計,緩兵之計是延緩對方進兵的謀略。當論辯局勢不宜速戰速決,或時機尚不成熟時,應避免針尖對麥芒式的直接交鋒,而應拖延時間等待戰機的到來。一旦時機成熟,就可后發制人,戰勝論敵。如在例子中,丘吉爾在時機不成熟時,不急于成功,以慢待機。在討論首相人選的關鍵時刻,以沉默表示反對,最終贏得了勝利。
其二,以慢施謀以弱克強
“以慢制勝”法適用于以劣勢對優勢、以弱小對強大的論辯局勢。它是弱小的一方為了戰勝貌似強大的一方而采取的一種謀略手段。“慢”中有計謀,緩動要巧妙。這里的“慢”并非反應遲鈍,不擅言辭的同義語,而是大智若愚、大辯若訥的雄辯家定計施謀的法寶之一。如在例子中,丘吉爾面對張伯倫的追問,裝聾作啞,拖延時間,實際上是假癡不癲的緩兵之計。在這一種韌性的相持中,張伯倫一方終于沉不住氣了,丘吉爾以慢施謀終于取得了勝利。
其三,以慢制怒以冷對熱
“慢”在論辯中還是一種很好的“制怒”之術。論辯中唇槍舌劍,自控力較差的人很容易激動。在這種情況下,要說服過分激動的人,宜用慢動作、慢語調來應付。以慢制怒,以冷對熱,才能使其“降溫減壓”。只有對方心平氣和了,你講的道理他才能順利接受。
總之,論辯中的“快”與“慢”也是一種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兵貴神速,“快”當然好。可是,有時“慢”也有“慢”的妙處。“慢”可待機,“慢”可施謀,“慢”可制怒。“慢”是一種韌性的戰術,“慢”是一場持久戰,“慢”是舌戰中的緩兵之計。緩動慢進花的時間雖長,繞的彎子雖大,然而在許多時候,它卻往往是取得勝利的捷徑。
上一篇:辯論的禮儀,服裝,儀態,心態
下一篇:淺談辯論的三點小技巧